https://read.douban.com/ebook/194624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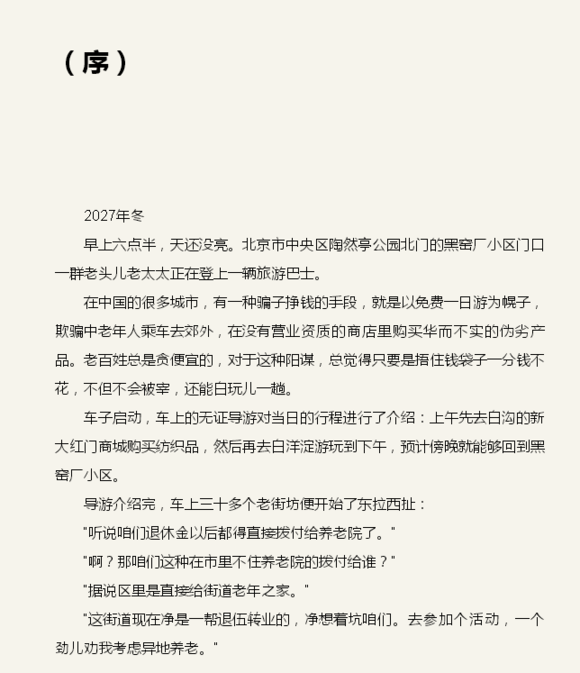
(一)
2032年的年末是一个极为寒冷的冬天。正在单位开年终总结会的我突然接到了固安区养老院打来的电话,院方通知父亲病危,正在友谊医院固安分院抢救,请我及时去当地处理相关事宜。
放下电话,我就去和坐在头排的领导请了假,走到地下车库取车,准备直奔固安。启动引擎之前,我给在国外陪读的孩子他妈发了个信息,“孩子爷爷病危,如方便可定最早机票回国,保持联系。”
开车到了红绿灯,一位交警将我拦下,示意我把车停到路边。停好车,交警走到车边向我敬礼,之后便问我:知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只有尾号1和6才允许上路行驶?根据规定,记6分罚款3000元。
我知道多说无益,便拿出手机,点开国家发改委强制所有手机安装的应用程序“发刻用”,选择里面的“发刻付”功能,一条二维码瞬间显示在了手机的屏幕上。
交警调试好机器之后直接扫走了我的3000元,之后把收据撕给了我,并说:“请于一小时之内驶离中央区。”
一个小时,从中央区的北二环行驶到西红门收费站,尽管只有尾号1和6的车辆在路上行驶,依旧是个挑战。车辆龟速行驶到菜户营桥的时候,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了电话,对方是个东南地区口音的男子,对我说我父亲二十年前做生意欠了他三百万人民币,如果我父亲去世,剩下的钱就要我来还,否则……我直接把电话挂了。我父亲退休之前就是个公交司机,跟谁能做上百万的生意?不过,我父亲病危的消息,似乎让不少不该知道的人知道了。
车流依旧向南龟速行驶。
交警告诉我的一个小时也早已过去,一路的探头必然已经拍摄到了我这样一个违规者的存在,一个又一个的6分3000元,这就是一个北京人在自己的家乡开车需要付出的代价。为了避免这样的代价,我的一些朋友铤而走险,将车辆的电子号牌信号发射器电线剪断并遮挡号牌,有的人干脆直接举家搬到了不受限行政策影响的廊坊、香河、张家口、涿州等北京新区或者干脆直接移民国外。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在中央区工作,或许我也早就和他们一起搬走了。
开过马家楼的时候,又一个陌生号码来电,这次是固安区的电话,似乎不是诈骗。接过电话,一个北方某地口音对我说:大哥,节哀啊!您雇医闹不?我们公司专业医闹业务水平老高了,还能帮打官司,你父亲×××不能白死,该讹他们一笔钱还得讹。获得赔偿支付时你拿六成,我们拿剩下的那四成。我直接挂了电话,第一个向我传达我父亲死讯的居然是专业的医闹公司。那个号码随后又多次打来电话,我直接拉入了黑名单。
五分钟后,固安区养老院打来电话,正式向我通知了父亲的去世,并通知父亲的养老账户已无余款,要求我尽快来固安结清欠费,办理后事。
父亲去世的那一刻,我居然被堵在京开高速四环路内的出京方向。我关上了车里的交通广播,此刻车速的快慢和路况的好坏已与我无关,我只想在车里这个封闭空间静静,安安稳稳地开到固安。车内宁静的氛围被手机传出的一条条短信声破坏,什么卖寿衣的、卖坟地的、卖假花的、卖纸钱的、一条龙服务的、什么遗产、房地产官司专业律师事务所等等,似乎父亲去世的消息除了我的其他亲友之外,全世界都知道了一样。当然,这些短信中还有一条是因为我一个小时内没有驶离中央区而收到的北京市交管局对我扣6分和罚款3000元的处罚通知。
关上短信,我打开微信的家庭讨论群,用语音向家人发布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各位亲朋好友,父亲×××刚刚在河北,啊不对,是北京固安去世。我现在在前往固安的路上,一个人开车看手机不方便,有什么新消息我会随后在这里公布,就不一一给大家回消息了。只有这些家人是我在无比伤痛的时候,唯一能想到的慰藉。
此时,我正驶过西红门收费站。这条京开高速上的钢铁长龙继续向南缓慢蠕地动着。
自从北京市政府2018年迁往通州之后,原先北京市的一些近郊区县,比如大兴、昌平、房山的市属资源便被迁移至通州,力求将通州区打造成和北京市中央区城市功能水平不相上下的服务北京市民的新型开放性城区。而大兴区,则被打造为首都新兴产业人才创业就业扶持创新区。为此,无数产业园区、办公大楼和人才公寓在大兴区广袤的土地上拔地而起。2024年,在一项针对全国高校学生的调查问卷中,63.7%的被调查者将北京市大兴区作为毕业后优先选择的生活工作目的地……
车流里突然一辆逆行的电动自行车向我冲了过来,我一脚刹车踩到底,后车躲闪不及直接给我来了个追尾。电动车的司机指着我说:你怎么开的车?
我下了车。后车司机也下了车,对着逆行的电动车司机说:这儿是高速路,你丫逆行是找死吗?
电动车司机还嘴说:你们开车就牛逼啊?你们是不是欺负我骑车的啊?我还不是为了给你们送外卖?没有我们,你们就等着饿死吧。说完,电动车司机往左一拐,抢行穿过两条车行道,逆着车流向北逃窜了。
后车司机想追,想骂,想打,但是车流滚滚,他又如何抓到在首都新兴产业人才创业就业扶持创新区引发此次交通事故的肇事者呢?
我们两人看了一下碰撞的部位,幸亏车速慢,后车和我只是轻轻一吻,前后车牌互相顶了一下。
后车司机对我说:大哥,真拿这帮不要命的傻逼没辙。您说这事儿怎么解决?
我说:得亏没碰着他,要不然不知道怎么躺地上装死讹咱们呢。追尾还能碰上个北京人也真不容易,不就车牌互相顶了一下么,各回各家吧。
后车司机掏出500块钱,执意要塞给我,我摆了摆手说:心意领了,钱你自己留着吧。
后车司机作了个揖,说:得嘞!呦,没发现,您这还是个新能源车,这都多少年了,这电池还能用呢啊?
我回答说:凑合用吧。
之后,我们就各自上车,一前一后地各走各路了。
我记得,新能源车,其实就是电动汽车,在20年前又不用摇号买,走在马路上也不用限号,说是为了支持首都环保,减少当时肆虐一时的雾霾。
后来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了,说机动车尾气是产生雾霾的原因,完全是为了推广新能源车,化解新型电池的产能过剩,协助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和地方政府套取国家新能源补贴。几年后,随着有关官员的落马,新能源汽车的环保伪命题也不攻自破,新能源汽车也不再享受不摇号不限行的政策。因为新型电池的生产产生大量污染和报废后难于处理的问题,新能源汽车电池也不再允许生产。在实际使用中,新能源车的电池也没有几年寿命,时限一到,整辆车就变成了废铁一堆。原先的新能源车主车辆报废之后只能重新参加机动车摇号或者车牌拍卖。
随后,国家要求北京的实际污染源——首都周边的所有工厂严格执行环保标准,但地方相关部门和工厂依旧阳奉阴违。几番拉锯战之后,国家索性借助“京津冀一体化”的东风将北京市界周边的几个区县划入北京市行政区划,在体制机制上达到了对污染企业的有效监管。当然,作为回报,北京市也将养老服务、医疗服务等诸多新兴公共服务业态迁往这些新区县,并利用各种政策手段或鼓励或强迫市民前往北京新区县享受有关公共服务。
当年,父母去北京新区县养老,子女在同等条件下是可以优先评优提干的。拿本人来说,我原本是开公交救援车三班倒的那种技术工人,我父亲不愿意让我这么辛苦,于是第一批就报名去固安异地养老,我也不用再三班倒,被调到运营分公司朝九晚五地负责文明乘车宣传工作。至于宣传管不管用,想必大家也心知肚明。倒是分公司拥有可以对新能源汽车电池进行维护的设备,所以我也有时以权谋私,用公司的设备维护新能源车的电池,车就一直这么开着。
父亲为了我,选择了在固安养老,如今他在固安去世,我正赶往固安,为他老人家办理后事,心里充满了悔意。
驶过大兴这个创新区,车辆依旧在缓缓蠕动。远远望去,干枯的永定河对岸那个“新北京,新南城”的大标牌已经在固安奶茶色的雾霾中依稀可见了,永定河大桥南岸的固安收费站到了。
虽然固安早已划归北京,但是这个原本的省界收费站依旧屹立不倒。也有人在之后的北京市两会上质疑这个收费站的合法性问题,官方的答复是:依照《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通过经济手段,对前往中央区方向的车流进行疏导,减轻中央区交通压力。
这样的疏导,每车次80元。当然,这样的疏导并不是针对每个人。身份证开头为131022的车主均可向区有关部门申请办理“南城通”车证,通过永定河收费站时,是不收钱的。也是借助手中的那点儿权力,我的车上有一个“市政公交抢险”的车证,可以糊弄一下固安区的道路收费员,在特种车辆专用通道直接免费通过。
于是,我便进入了固安区,我父亲离世的地方。
驶出高速,进入固安的车流便被引道上的一干人等团团围住,他们拍着京牌车辆的窗户挨个询问,“大哥,买房吗?”、“大哥,找养老院吗?”、“大哥,找医院吗?”、“大哥,雇医闹吗?”、“大哥,找火葬场吗?”、“大哥,买墓地吗?”……
我按着喇叭往前开车,但在心里回答着:什么都不用买,一切都在北京预备好了。活着被骗出来,死了必须得埋回去!
与河对岸的大兴区的蓝天白云不同,固安区的天空雾霾一片,天空蓝白色的分界线,就在早已干涸的永定河河床。为什么永定河两岸的天空如此泾渭分明呢?这里也有段故事:
2030年,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发给了主管经济、科技、体育、环保事务的北京市副市长,中科院院士罗宁。罗宁院士原本在一家央企从事金融投资工作,为大家所知的身份是央企董事长助理和足球俱乐部名誉主席,其实,他所在的集团内部有一个秘密环保实验室,二十多年前便开始秘密研究如何对雾霾进行有效治理。罗宁院士在发表的论文中也强调:治理华北地区雾霾,仅仅依靠冷空气吹散和产业减排是无法达到显著效果的;天气无法控制,产业减排会影响企业经营,加剧失业,为地方财政造成负担,既有损多方利益,又严重违背市场规律。
经过多年潜心钻研,罗宁院士领导的秘密环保实验室研究出了一种“纳米静电丝”。这种“纳米静电丝”具有坚韧属性,并可以通过导电来吸附PM2.5尘埃,经过在大兴创新区实验室的初步论证和实验,2021年,该实验室将数万跟长度近百米的“纳米静电丝”按照一定排布组合竖立在了大兴创新区内的永定河北岸。测试的效果是喜人的,赶上南风的时候,从华北平原扩散而来的雾霾被死死地挡在了永定河南岸。罗宁院士因此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并破例被增选为中科院院士。当然,这一专利技术带来的收益也是相当惊人的,许多国外公司也对这项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北京的街头巷尾又多了个歇后语,叫“别和罗总比有钱”,没错,他做到了!
此后的北京,日日蓝天。遗憾的是,当年北京市某个喊出“提头来见”誓言的领导并没有在生前见证蓝天的回归。媒体和民众们也顺理成章地开始对之前那些大肆叫嚣机动车尾气是北京市首要污染源的专家学者们进行质疑和责问。质疑的结果就是大量官员落马,新能源汽车不再享受免摇号和免限行政策,但北京市机动车车牌摇号和拍卖的政策依旧实施。
大量雾霾的堆积导致视线受阻,我的车依旧在混乱的固安街道龟速行驶。“新北京,新南城”,这似乎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货真价实的北京城的三不管地带,黑摩的横行,马路中间要饭、卖东西、插广告、碰瓷的,街边遍地烧烤大排档,居民楼的一楼被拆墙打洞,变成了各种无证照商店餐馆……路边一个老年公寓楼的墙面广告“固安,还您老北京城的念儿想”这句标错儿化音的广告词不知道算是安慰还是讽刺。
在医院停车场入口排了差不多半个小时队并和几辆企图加塞儿的车多次较劲之后,我终于来到了北京友谊医院固安分院,我的父亲三个小时前就死在了这里。


